确诊了HIV感染,并发淋巴瘤
“我觉得对不起我家里人啊……是我做错了。”
作者
宋晓璟
来源
摘自书籍《协和医事》
1年2月15日6点45分,北京仍是冬天的气派,得靠着黑咖啡才能提神的又一个早晨。在地铁上,我收到了一位老病人的信息,要送给全体感染科的医生护士们。HIV感染加上淋巴瘤化疗,印证了那句话,痛苦会催生好的诗篇:
我不能以诗歌的名义,
占领我这整个冬天。
我不想以燃烧的方式,
掠夺我的缠绵。
这冰冷或温暖的茶啊,
还要伴我数年。
隔着这降温的夜空,
我感到心里的升华。
这分明是春天的意境,
这分明是一份无语的留恋。
医院旁,窄窄的柏树巷子里,
驻扎着我难忘的时光,
一不小心,
也就爱上了我的似水暮年……
日子走得和你一样慢,
慢得没有了季节与时间。
把清晨打开,
再冷也是春风拂面。
把黄昏打开,
更珍惜这掠过的一、二、三期步履蹒跚。
时光的最深处,
我看见或看不见的都是遇见,
都是满心的期待与柔软……
此刻,我醉心于你的目光如炬。
感觉你在向我召唤。
此刻,你把我写成了二月的诗篇。
感觉五月的风也在把我召唤,
知道吗?我有着多少,对人生美好的眷恋,与浪漫……
这是一位62岁的男性病人,检查到HIV感染的同时,发现了淋巴瘤。这首诗写成正是在他完成第二程CHOP(一种化疗的治疗方案]的休疗期)。诗中可以看到他的细腻、他的感激还有对生命的无限留恋和渴望。
不同于艾滋病门诊的一般患者,第一次见面,是受感染科医生委托,背着电脑和资料到病房为他做ART(AntirtroviralThrapy,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是治疗HIV感染的一种手段)治疗前的咨询,这是一个理智、克制、极为敏感的人:穿着病号服,扣子系得一丝不苟,虽然刚做了骨穿,仍然平整如新的床单。眼神里有着沉沉的压力。
今天咨询的目的是让他了解即将开始的ART治疗的目的,以及依从性的重要性。说明了来意和身份,我陈述了病人隐私保护的原则,经过他的同意,把他的夫人和儿子也请到床边一起旁听。打开PPT的第一页,罗列着初诊常见的问题:
“我还能活多久?”
“要怎么治疗?”
“会传染给别人吗?”
“和家人生活在一起需要注意什么?”
“我还要办理什么手续?”
看到这里他取出了老花镜,显然这是说到他的心里了。
患者的学历是本科,这让我们接下来的交流容易了许多。对于还能活多久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给他完美的答案,因为专业的限制,我只能提供欧美国家基于HIV感染的关于存活时间的一些研究结果。但是这个病人更为特殊,HIV感染的情况发现得相对比较晚,现在还存在淋巴瘤的问题,淋巴瘤的治疗效果可能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影响更大。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有机会,活下去的机会,对任何一个病人来说都弥足珍贵,哪怕他是感染了HIV。
毫无疑问,面对HIV合并淋巴瘤的患者,压力要比平时更大一些,但是病人的反应很不错。一个小时的咨询马上就结束,余下的问题就留给感染科、血液科的各位专家才能回答了。
病人让家属全都出去,问我:“在你的印象里,有淋巴瘤的那些病人都怎么样了?你说实话。”我回答:“这样的病人并不是很少,但是在我的印象里,他们都没有放弃过治疗,有还在治疗的,也有恶化的,也有离开的。可以肯定的是,治疗没有那么容易。”
病人的情绪像是忽然间决了堤:“我觉得对不起我家里人啊……是我做错了。”
之前看了病历的我当然知道他在懊悔什么,感染科对于专科护士的培训也包括了这一部分,静静地等待他安静下来,我说:“其实您决定把病情告诉家人,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家人负责任的表现。你生活的一部分会发生改变,充满挑战。”提供信息,提供支持,帮助患者应对眼前的困难,帮助他们过一种有尊严、有质量、负责任的生活,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目的。
第二次再见面,是一个星期以后,我去看这个病人服药的情况。还是那张病床,病人的精神好了很多,正输着液,一进门他就坐起来了。“太感谢你们了,在这儿我没感觉到一丝一毫的歧视,你们感染科的医生护士包括血液科的专家都对我特别尽心。”那一刻,我确实开心,一个能心平气和跟你谈论歧视的病人,首先是肯定你不歧视他的,医护人员和病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也是治疗的一种手段。护士长也是每次都说,HIV感染的病人最好交流,其实这正是所有感染科的护士对艾滋病患者态度的回应啊。以上种种,造就了开篇温柔的小诗。
艾滋病合并淋巴瘤,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那些病人的故事,有的明亮,有的悲伤。非常幸运,他们可以得到医院医护人员的帮助和照顾,这让他们在“不放弃”这条路上走得格外坚定。
2想起有一个腹腔淋巴瘤手术后的男病人,比我大十多岁,块头也比我大一倍,每次在医院走廊里遇见他,都躲闪不及,被一个胖乎乎的汉子“熊抱”然后叫着“姐姐、姐姐”的愉快想必不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病人很坚强,术后的化疗也配合得很好,出了深静脉血栓也治疗得不错,定时复诊中。
32
另外一个男病人,瘦削、精明,刚刚开始抗病毒治疗,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在就诊流程和领药方面有着这样或那样特殊的要求,我跟着资深的李护士一起出门诊,一起见病人,也一起面对着他制造的各种问题。
治疗了不到半年,有一天病人打电话来,说是爬山后大腿一直疼,可能是扭伤了。但又问我跟这个病有没有关系。我只好回答:“你必须要看门诊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要么看外科,要么来我们教授的门诊,不能靠不见面乱猜。”
后来,外院当作蜂窝织炎治疗一周未见好转,经过李太生教授的诊疗和后继的检查,诊断为淋巴瘤。记得第一程化疗还没有结束,一个中午,我被当班同事叫去帮忙抢救,那是我见到这个病人的最后一面。在那之前,在感染科病房里无数次碰面,都觉得尴尬,完全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也就是听他说着他副作用反应厉害,说他疼啊难受什么的那些时候。刚成为艾滋病专科小新人的我,觉得自己根本就帮不上什么忙。
之后的一周,被借调出去参加一个活动,再回来是一周之后了。一进办公室门就看见桌子上放着蓝色的小盒子,李护士告诉我,是这个病人去世以后,他的妹妹送来的,是去世之前病人给定做好的,我俩一人一个。打开盒子,是一枚银质的项链,坠子是一本小书,居然可以翻页,依稀可见上面的文字:
Andforgivusourdbts,aswforgivourdbtors.Andladusnotintotmptation,butdlivrusfromvil……
译: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
我知道这是圣经的主祷文,他已经去了天堂。其实我们对他并没有特殊的照顾,所以这份礼物给予我们的,远远比我们给予他的要多。
对比之前的病人,现在的艾滋病专科团队可以做的更专业,更完善。然而,只靠感染科和艾滋病专科团队,是无法给病人全面的治疗和照护的。
《实习医生格蕾》(著名美国医疗剧,女主角名“格蕾”)里面有一集,格蕾的大咖妈妈和主任年轻的时候给一个AIDS病人做疝修补手术,其他人都吓疯了,明亮梦幻的镜头感提醒我们那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我的美国同学在手术室工作,对于手术中被划伤而感染HIV的比例有多小,她的同事们都有共识,反而是丙型肝炎是她们最为担心的问题。年的BMJ一篇综述里面,Riddll和Knndy等多位学者对近30年pubmd数据库和cochran图书馆的所有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提到乙肝病毒、丙肝病毒和HIV经锐器伤传播的风险常被引用为1∶3,1∶30和1∶。自年起,英国仅有1例医疗工作者职业暴露后出现HIV血清阳转(指血液HIV病毒抗体检测阳性),而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也已经几乎没有新的HIV职业暴露确诊病例发生。这不仅仅是因为暴露后预防治疗措施的联合应用更为有效,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HIV感染者懂得去定期检测,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使他们血液中的病毒载量基本在接近于0的水平,极大地减少了感染其他人包括医务人员的风险。
治疗手段在不断进步,我们对艾滋病的认识也在不断进步。没有哪个疾病的治疗能够引起这么广泛的
转载请注明:http://www.ednrm.com/wazz/11179.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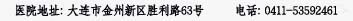
当前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