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皮肤科CPC2
患者男,53岁。
主诉右上肢结节,脓肿4月余
现病史4月前患者无明显诱因右手无名指及小指末端指节曲侧及其手掌部疼痛不适10余天,于当地诊所行曲安奈德局部注射治疗。次日出现一圆硬币大小的红斑,无明显痛痒不适。1周后沿右上肢内侧逐渐出现数个黄豆至花生米大小的丘疹,结节,呈串珠样排列,自觉疼痛,按压加重。在当地诊所予以抗生素治疗后,皮疹进一步增多,至我院皮肤科门诊就诊,组织病理检查示肉芽肿病变。诊断为皮肤孢子丝菌病,予以伊曲康唑及碘化钾治疗,右上肢丘疹结节短暂缩小,疼痛减轻。但2周后结节再次变大,数目增多,手背结节出现脓肿,破溃后有脓液渗出。
既往史既往有糖尿病1年,口服降糖药控制血糖正常范围。
皮肤科情况右手臂及手背部见数个呈串珠状排列的、蚕豆至樱桃大小的暗红色结节,右手背及手腕处多发暗红色脓肿,有轻微波动感实验室检查结核感染T细胞斑点实验(-),胸片无异常。
病理学特征真皮深层见大量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组织细胞、多核巨细胞及浆细胞呈弥漫性浸润。
抗酸染色阳性。
穿刺脓液涂片抗酸染色阳性。
基因芯片技术鉴定为脓肿分枝杆菌。
诊断皮肤脓肿分枝杆菌感染
治疗抗结核治疗予以克拉霉素(mgbid)、乙胺丁醇(0.75gqd)及利福平(0.45gqd)口服。治疗11天后,患者手背部脓肿较前明显缩小,未触及波动感,右前臂及上臂结节较前缩小。治疗42天后,患者皮疹进一步缩小。6个月皮损完全消退,遗留色素沉着和瘢痕。随访3个月未见复发。
讨论脓肿分枝杆菌是一种快速生长的非结核分枝杆菌,最早由Moore和Frerichs于年发现,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土壤和水中,在人体中主要引起肺部及皮肤软组织的感染。既往脓肿分枝杆菌感染的发病率低,但近年逐渐上升,需引起我们的重视。感染主要通过伤口(或导管或其他暴露的表面)与环境(存在脓肿分枝杆菌的水、土壤)或受污染的设备(手术器械、针等)直接接触而发生。由于脓肿分枝杆菌对一些消毒剂如氯、甲醛、碱性戊二醛及有机汞制剂等具有抗性,常规的消毒方法常难以根除。有报道近45%的皮肤脓肿分枝杆菌感染发生在手术后,随着医疗美容行业的发展,目前脓肿分枝杆菌的感染多发生在抽脂、面部除皱、隆胸和其它有创操作后(如纹身、注射、针灸等),不恰当的灭菌技术可能是有创操作后感染脓肿分枝杆菌的主要原因。本例患者的感染发生在局部注射治疗后,糖尿病病史增加其易感性,注射药物曲安奈德降低了局部皮肤对感染的抵抗能力,以上均为脓肿分枝杆菌感染提供了条件。
患者皮疹为单侧串珠状排列的结节、脓肿,病理表现为肉芽肿性炎,根据临床经验极易诊断为孢子丝菌病。临床常见的孢子丝菌病(淋巴管型)典型表现为沿淋巴管呈串珠状排列的暗红色结节,可出现化脓及溃疡,组织上的病理改变为混合性炎性细胞肉芽肿。但是该患者抗真菌治疗无效,最终通过分子生物学方法,确诊为皮肤脓肿分枝杆菌感染。皮肤脓肿分枝杆菌感染可表现为结节、疖肿、蜂窝织炎样皮疹、脓肿及溃疡,形态多样;病理常表现为化脓性肉芽肿性炎,临床皮疹及病理均无特异性。但表现为类似孢子丝菌病串珠样分布的结节样皮疹较为少见。
病原学诊断是诊断本病的金标准。脓肿分枝杆菌的检测方法包括临床标本抗酸染色涂片镜检、分离培养鉴定和分子生物检测等。涂片抗酸染色是一种快速可行的诊断方法,缺点是敏感性低,不能鉴定菌种。传统的鉴定方法即表型鉴定,通过观察菌落的特征如生长速度、色素产生、菌落形态和生化反应等来推断菌种,但步骤繁杂,耗时长,且培养的阳性率受取材,培养基以及前期用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分子生物学技术检测手段包括16SrRNA基因测序、hsp65基因测序、rpoB基因测序、核酸探针、基因芯片、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MS)等。基因芯片可较为精准的区分及鉴别多种非结核分枝杆菌,是目前较为可靠的分子层面的鉴定技术。该患者采用基因芯片方法最终确定为脓肿分枝杆菌。
治疗上,脓肿分枝杆菌对大多数抗生素及抗结核药物不敏感,但是普遍认为脓肿分枝杆菌对克拉霉素、阿米卡星、头孢西丁及亚胺培南等具有一定的敏感性。目前脓肿分枝杆菌的治疗还没有一个标准的治疗方案,通常采用多种抗生素联合应用。本例患者联合应用克拉霉素、利福平及乙胺丁醇口服,皮损在治疗6个月后完全消退。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ednrm.com/wadzz/14343.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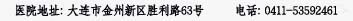
当前时间:
